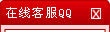但 有 诗 书 润 我 心
黄冬松
那天,一位记者朋友来采访一起案件。他发现我的书橱里除了厚厚的法律书籍外,居然还有一些诸如《诗经》、《唐宋词鉴赏》、《文学与生存》等文艺书籍。在他的印象中,法官整日忙于定分止乱,特别是刑事法官,面对着种种罪恶,平日以冷峻示人,不苟言笑,充满着理性,哪有如此闲情逸致?
也有人问我,长期从事法律职业,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我想起沈从文先生《边城》里的翠翠,我们其实和她一样:等着渡人,等着人度。

渡人者,先度己。
何以渡人,何以度己?
这本不是一个问题。早在1910年,德国法律思想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就在他的《法学导论》中提出,刑事法官要将歌德在“马哈德,大地之王”中所说的话铭刻心上,即:他应惩罚,他应宽容;他必须以人性度人。
西方法谚有云: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法律从恶人假定的角度设计,而司法者本身的品性更值得寻味。我曾经问过一位年轻的法官:在你办理案件时,你是否流过泪?她的回答很俏皮:案结事了!我在想,如果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是否就像在阅读一幕悲剧,我们能够感同身受,随当事人悲伤。在提醒自己保持中立的同时,自己也有一种锥心的痛?为一个个体,为一个群落,为这个社会最深层次的东西。如果是这样,公正作为一种力量,自然会积聚。无需挂在嘴边,无需写在纸上。
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发现,因为职业的原因,长期接触罪恶、贪婪、狡诈等人性中恶的东西,自己也好象染上一种职业的弊端——冷漠,内心越来越坚硬。一个冬日的中午,在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忙碌之后,我静静地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手捧一本赏析纳兰性德的词的书,遥望白云,阳光暖融融地照在身上,也照进心里。不觉得,渐入迷糊状态,手一松,那本书悄然落地---何等惬意!不仅仅是惬意,更重要的是,纳兰词在无形之中,“像一道道疗伤的温泉汤药,温暖了,唤醒了,我们冰封的情感。”
法律,有他固有的逻辑和理性。他讲求法理、情理、事理、文理的和谐与统一。优秀的法律人不是工匠,而应是一位工艺师。每一件面向公众的法律产品,就像那一只温婉的紫砂壶,凝聚着制作者内心的志趣和心性。触摸法律,从他的材料、质地、纹理中,我们不仅要
感受法律的精神,而且还必须明白,他从多么深的生活中产生?我们又怎样将他归于生活?!
捧读法哲学,我们充分关注法律的基本价值: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轻读诗书,我们关注人性、关注命运,领悟书中弘扬的人文精神。正如著名学者林东茂所说:法的评价与美的审查,都在作价值判断,两者虽然在不同方向走自己价值判断的路,但终极目的都在创造喜悦,都有诗的感觉。在法治的田园独步,我也办理了形形色色的案件,见过各色人等,读过一些书,写过一些文章,可是总是停滞在不敢恭维的层面上,总是缺乏一种高度,一种引领,越来越有一种无以突破的感觉。我一直在想,法律的理性与诗的唯美如能兼容,该是一种怎样的艺术?若能沉潜下去,融通法理、文理,写就一篇能够诵读的裁判美文,既法理昭昭,又文采斐然,又该是怎样的欣喜?——这是一种功力!古人能够做到,而我们如今却大都只能企望。
传说中,干将、莫邪为吴王铸剑时,辛苦三个月,却因为炉中采自五山六合的金铁之精无法熔化,剑无法铸成。有一天,干将在泪光模糊中,看到莫邪站在高耸的铸剑炉壁上,裙裾飘飞,宛如仙女,飘然坠下…… 宝剑因融入莫邪的挚爱和精魂终于铸成。而我们是否要在法律的理性中融入诗的灵性,才能从对生命意识个体的省察和体悟中感受神圣的使命?!
据说,武术的境界有三: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而我们,以法律为职业的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只须在案情和法律条文之间建立一种逻辑上的联系,如若在法治的帝国不被世俗浸染过多,葆有一种激情和向上的力量,能够在俗务中超越,从而寻求事业的归属,寻求一种审美,真的需要一种指引与洗涤。
——但有诗书润我心,但将诗心融法理!
——————————————————————
作者简介:黄冬松(1970—),男,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