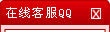盗用他人医保卡号冒名取药的行为如何定罪
刘 斌
内容提要: 盗用他人医保卡号冒名取药的行为构成何种犯罪,我国刑法并没有对此作出特别规定,这种欺盗结合型犯罪,犯罪人的行为中既有秘密窃取的行为,又有欺骗的行为,是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区分关键在于两种行为之间哪种行为为哪种行为创造了条件,行为人取得财物是在被害人处于何种情形之下取得的。
关键词: 盗用 欺诈 结合
案情简介:
被告人陈某,男,1972年12月13日出生于A市B区,汉族,高中文化,原系A市B区某矿业公司职工,住A市B区C村102号。被告人陈某于2007年年初,从某矿业医院抄走在医院住院的矽肺病人名单的同时拿走空白医保卡十余张,后在A市某复印店将该矿矽肺病人的姓名和医保卡号打印到空白医保卡上。在2007年1月至2008年3月期间,被告人陈某利用伪造的医保卡,谎称替矽肺病人开药,在A市B区医院和某职工总医院等处开药,计药品价值人民币23148.4元。又于2008年5月4日至12月1日,从某矿业医院抄走申某等30余人的医保卡号,后凭医保卡号谎称受人委托,从A市B区医院、某职工总医院等处替人开药193次,计药品价值人民币62821.35元。并将开出来的药品低价转卖给附近城镇的个体诊所,共获利4万余元。案发后,被告人陈某于2008年12月18日向A市公安局B区分局C派出所投案自首。公安机关以其涉嫌盗窃罪于2008年12月18日对被告人陈某予以刑事拘留,2009年1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A市看守所。
A市B区人民检察院以指控被告人陈某犯盗窃罪,于2009年5月27日向A市B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A市B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在庭审阶段,公诉人认为,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医保卡号,伪造和冒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低价销售,所售药品共计价值人民币89969.75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陈某采取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药品,而不是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非法占有药品,因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且诈骗数额巨大,应以诈骗罪定罪量刑。
本案的焦点在于:(1)、关于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定;(2)、关于数额特别巨大与数额巨大的
界定。
法理分析:
根据《刑法》第264条、第266条之规定,所谓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所谓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诈骗罪与盗窃罪,两罪主体都是一般主体,凡年满16岁具有刑事责任力的自然人,都能成为其犯罪的主体。两罪的客体都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犯罪对象都是公私所有的各种有价值的财物。两罪的主观方面都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两罪之区分只是在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诈骗罪是以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骗取财物所有者或控制者的信任,“自愿”地交付财物。盗窃罪是以秘密窃取的方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在秘密窃取的情况下,行为人取得财物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取得其财物。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陈某构成盗窃罪的理由是,(一)、被告人陈某从某矿业医院抄走他人的医保卡号,冒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低价销售,是秘密窃取。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主观上自认为采取公私财物的所有人、管理人不会发觉的方法,将财物非法占有的行为。(二)、我国刑法对盗取他人医保卡或者医保卡号冒名取药的行为并没有作出特别的规定,然而,我国刑法对盗用他人的信用卡、电信卡、网络上网帐号、IC电话卡、通信线路、电信码号牟利的行为作了特别的规定。《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2000年5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将电信卡非法充值后使用,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第8条又规定:“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帐号、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2003年4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法制作、出售、使用IC电话卡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明知是非法制作的IC电话卡而使用或者购买并使用,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65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陈某盗用他人的医保卡号,复制他人的医保卡,冒用替人开药低价销售,形式上与传统意义上直接获取财产的盗窃行为有所区别,但行为人是以不被被害人发觉的秘密手段实施的,其结果也是让被害人的财产遭受损失,因此,本质上与传统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并无不同。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陈某构成诈骗罪的理由是,被告人陈某使用了欺骗的方法,使受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而“自愿”交付财物。被告人陈某第一种作案手段是在伪造别人的医保卡后,谎称替他人开药,医务人员在相信其谎言后,将药品开给被告人陈某。第二种手段是被告人陈某在获取持卡人姓名及医保卡号后,谎称受他人委托,替人开药,医务人员继续轻信被告人陈某,将药品开给被告人陈某。两种手段,被告人陈某均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作为个人医保账户的保管人的医务人员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将药品开给被告人陈某。如果医务人员没有发生错误的判断,被告人陈某仅凭医保卡号则无法达到开药的目的。另外,盗窃罪的行为中秘密窃取是由行为人单方完成的,不存在财物所有人、保管人的参与配合。

笔者赞同辩护人的观点。所谓欺骗方法,最常见的是隐瞒真相和虚构事实二种,“虚构”和“隐瞒”是就行为方法而言的,“事实”和“真相”是就行为的内容而言的。虚构事实,是指行为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无中生有”地诱使他人上当受骗。虚构事实可以是无中生有地全部虚构,也可以在部分事实的基础上渲染夸张地部分虚构,前者如没有货源而虚构有货源,后者如只有少量货源谎称有大量货源。本案中的被告人陈某谎称替人开药,“无中生有”地诱使他人上当受骗。隐瞒真相则是指隐瞒客观存在的某种事实,欺骗被害人。如行为人将镀金首饰冒充黄金首饰品出售。本案中的被告人陈某复制、伪造别人的医保卡和医保卡号这一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欺骗医务人员。实际上,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往往交织在一起,都是以有掩盖无,隐瞒真相可以辅之于虚构的事实;虚构事实同时就会隐瞒真相。本案中的被告人陈某复制、伪造别人的医保卡和医保卡号与谎称替他人开药就是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地诈骗医务人员。所谓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自愿”交付财物,即行为人使用各种骗术达到了使被害人“信以为真”的程度,其结果是“自愿”地交付财物让行为人占有,即从表面上看,行为人交付财物是自愿的,实质上这种“自愿”并不是财物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真实意愿,是被行为人造成的假象所迷惑的结果,也就是说,是被害人事实认识错误所致。而这种事实认识错误是行为人故意设置的。因此,行为人的欺骗与被害人的信以为真的自愿交付财物是紧密联系的。如果行为人使用了欺骗方法后很快被识破,被害人没有信以为真,就难以构成犯罪的既遂。欺骗方法的表现形式多样,如伪造、涂改证件,编造谎言,假冒身份或受他人之托,以帮助他人看管、提拿、代购、代卖为名,以恋爱、结婚为诱饵等骗取钱财。
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中的被告人陈某抄走别人的医保卡号确实是“秘密窃取”的行为,这也正是对本案被告人陈某的犯罪行为的定性是盗窃还是诈骗争议的原因所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欺盗结合型犯罪”的情形,一种是先欺后盗,欺骗是为盗窃创造条件。如行为人到商店购买项链,从营业员手中拿到项链后,趁营业员找零钱时的不注意,将随身携带的镀金项链予以掉换,类似这种行为,仍然应以盗窃罪定之。因为,从本质上看,先前的欺骗行为只是为了秘密窃取制造条件,受害人并没有在受欺骗的情况下,“自愿”将财物交给行为人。行为人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秘密的手段将财物占为已有的,应为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一种是先盗后欺,盗窃是为欺骗创造条件。被告人陈某抄走别人的医保卡号是陈某自认为没有被别人发觉的秘密窃取的行为,然后谎称替人开药骗取医务人员的信任取走了药品,类似这种行为,应以诈骗罪定之。因为,从本质上看,先前的窃取行为只是为了诈骗制造条件,受害人并没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财物被行为人秘密窃取。行为人是在被害人信以为真自愿交付后获得了财物,应为诈骗罪而不是盗窃罪。
至于我国刑法对盗取他人医保卡或者医保卡号冒名取药的行为没有作出特别的规定,却依据我国刑法对盗用他人的信用卡、电信卡、网络上网帐号、IC电话卡、通信线路、电信码号牟利行为的特别规定,从而认定被告人陈某的犯罪行为是盗窃罪,是极其错误的。根据法条竞合犯之适用原则,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竞合时优先适用特别法条,而法律对某种犯罪行为没有作出特别规定的,毫无疑问地应当适用普通法条之规定。如果法律对某种犯罪行为没有作出特别之规定,能够采用相类似的犯罪行为之法律特别规定而定罪,那么,对被告人陈某的犯罪行为也可适用《刑法》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之规定,认定被告人陈某构成诈骗罪。该条第1款第(一)规定:“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该条第1款第(三)项规定:“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均认定是信用卡诈骗罪,从而认定被告人陈某的犯罪行为是诈骗罪。虽然《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与第196条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从欺骗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我国刑法对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行为作了例举式的规定。而且类推似地适用刑法之规定,根本上也违背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被告人陈某犯罪数额的确定随着犯罪性质的确定迎刃而解。被告人陈某所售药品共计价值人民币89969.75元,根据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二)项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该条第(三)项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1998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也作了相同的规定。根据1996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意见问题的解释》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如果认为被告人陈某的犯罪行为定盗窃罪,其犯罪数额应当是“数额特别巨大”;如果认为被告人陈某的犯罪行为定诈骗罪,其犯罪数额应当是“数额巨大”。
﹡作者:刘斌,男,安徽众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铜陵学院客座教授,铜陵广播电视大学客座教授。
参考文献:
[1]孙国祥主编.刑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张明楷著.刑法学(上、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赵秉志主编.刑法学(上、下)[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
- 上一篇:黄某法律援助案解析
-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