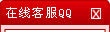如何认定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
——兼论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
刘 斌 谈春明
内容提要 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的一种,格式条款绝大多数都是由保险人事先拟定反复使用的条款,因而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具有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和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义务。然而,足以引起注意的标准与明确说明的程度或标准是什么?我国《保险法》没有具体规定。在格式条款产生歧义、发生纷争时,应当首先采用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只有在对格式条款有两种及两种以上解释时,才采用不利解释的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 格式条款 免除责任 明确说明 不利解释
案情简介
盈安运输公司所有的皖B42756号自卸货车使用性质为营业货车,在天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机动车损失险等商业保险,其中,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27万元,保险期限2011年6月16日至2012年6月17日。盈安运输公司驾驶员杨某驾驶该自卸货车于2011年8月6日在铜陵市兴港码头卸货时侧翻,导致该车辆严重损坏。天安保险公司以机动车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车斗未放下导致的车辆损失及第三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保险人不予赔付”之约定,于2011年8月12日向盈安运输公司下达了《机动车保险不受理索赔案件通知书》。
盈安运输公司于2011年11月25日提起诉讼,并向法院提交了兴港物流公司于2011年11月12日出具了该自卸货车事发当日在铜陵市兴港码头卸货时侧翻的书面证明:“兹有皖B42756号货车2011年8月6日在我铜陵市兴港码头卸货时侧翻。特此证明。”认为属于保险事故,天安保险公司应当支付保险赔偿金。
天安保险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投保单,证明投保单上清楚记载了投保人自己填写的特别约定的内容,并提交了投保人盈安运输公司在投保时签署的《车辆投保过程确认承诺函》:“投保人在投保时确认贵公司提供的投保单已附本人投保险种相对应的保险条款,并向投保人说明了条款的内容。”认为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保险单(正本)的特别约定,属于免除责任范围,天安保险公司不予赔付。
争议焦点
一、如何认定保险人对免除责任条款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换言之,天安保险公司是否对特别约定“车斗未放下导致的车辆损失” 不予赔付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二、如何解释“车斗未放下导致的车辆损失” 不予赔付的免责条款?换言之,如何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法理分析
一、仅有投保单的记载和确认承诺函,并不能足以证明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之义务。
究竟应当如何进行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明确说明的“明确程度或标准”到底应当是什么,一直是保险合同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
《保险法》第17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从此条规定看,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的普通条款或曰一般条款,具有说明之义务,而对于免责条款则具有明确说明之义务;普通条款说明义务是保险人在向投保人提供投保单附格式条款时,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是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若保险人对普通条款未履行说明之义务并不一定导致普通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若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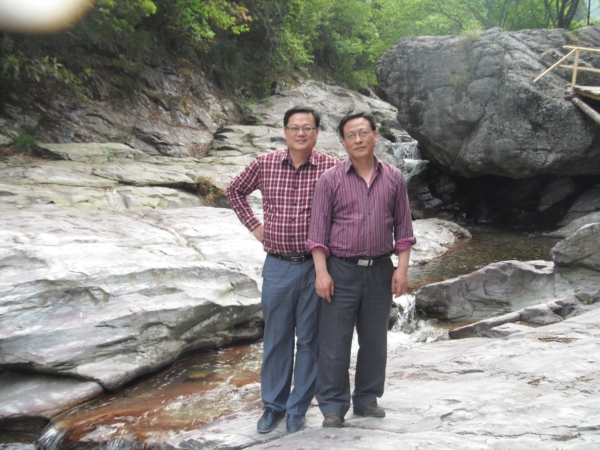
(一)明确说明的形式与时间。
依据《保险法》第17条之规定,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形式,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
根据《合同法》第11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之规定,保险人以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应当都是合法的履行方式。当然,明确说明也可以以书面和口头相结合的形式做出。
在保险实践中,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用粗体文字印刷免责条款,或者向投保人附送免责条款说明书,或者在保险单中设计投保人声明栏,声称保险人已经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进行了说明,投保人已经对于保险合同具有了充分的理解等等。但是,即使以此种方式进行了说明,投保人也不一定能够注意到免责条款的重要性或者理解免责条款的意义,也看不到保险人具有让投保人对免责事项明确知晓的主观诚意。因此,法律并不限制明确说明的方式,唯侧重在于明确说明的程度或效果①。
依据《保险法》第17条之规定,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时间是在订立保险合同之时。
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时,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是为了使得投保人明确保险风险的范围,以决定是否购买该保险。若保险合同订立时,因为保险人未尽到明确说明之义务,而使得投保人对于所购买的保险范围发生了误解,即使事后投保人明白了承保风险的真正范围,对于投保人而言仍然是不公平的。当然,若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后,保险人才进行明确说明,投保人明确表示认可并同意免责条款继续有效,则依据当事人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免责条款也可以有效。
本案中,天安保险公司在向投保人提供投保单时,投保人盈安运输公司自己在投保单上填写了特别约定的内容;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盈安运输公司签署了《车辆投保过程确认承诺函》。应该说天安保险公司履行免责条款明确说明的时间与形式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明确说明的履行标准应当以正常人能够知晓和理解为标准。
为了控制风险,保险人在拟定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时都会规定免责条款。而免责条款多由保险术语、法律术语和医学等专业术语组成。一方面,在密密麻麻的保险合同条款之中,投保人不易发觉免责条款的存在。另一方面,即使投保人注意到免责条款,由于当事人双方在专业知识上的信息偏差,投保人很难准确理解免责条款的含义及其法律后果。因此,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并且还是强制规定之中的效力性规定,即一旦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也是主动性义务,在投保人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保险人也应该主动进行说明。
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是使得投保人充分、确实地了解了免责条款的内容、含义和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2000年1月24日法研[2000]5号)中规定:“这里所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1条规定:“保险法第十八条中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做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保险人对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说明义务。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不因其他分支机构已与该投保人订立有同类保险合同而可以不履行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观点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签复大致相同。
遗憾的是,《保险法》对于明确说明的程度或标准没有规定。从《保险法》第17条规定来看,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要求保险人履行两个互相相关联的义务:一个是对于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另一个是对于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而提示义务是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前提。因为保险人没有提示投保人注意到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也就无从谈起。对于提示义务的履行,法律规定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即只能是书面方式,不能是口头方式。实践中有很多保险公司在格式条款中用黑体字、粗体字印刷免责条款,或者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之外,专门制作《免责条款说明书》,并要求投保人签字确认。上述提示方式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认为保险人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提示义务的履行仅限于订立保险合同时出示,不包括保险合同订立之后出具的相关凭证。提示的效果应当是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否则,仍然不能认为保险人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所谓“足以”引起注意的标准,是一个客观标准,应当结合履行的方式、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进行判断,侧重于提示的效果。而本案中,天安保险公司采取的是在投保单上由投保人亲自书写,并在保险单上作了特别约定,且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该说符合法律之规定,换言之,天安保险公司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
明确说明的标准有主观与客观两种标准。前者以说明人自我感觉为判断标准,后者以对方当事人对于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程度作为判断标准。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是后一种标准②。笔者认为,明确说明的标准应当采用以客观标准为主、特定情况下结合投保人自身理解能力作为履行标准。一般情况下,应当以投保人作为普通智识之人作为标准。若投保人的生活经验、专业知识和以往的投保情况会对免责条款的理解产生重大影响,可以结合上述特殊情况加重或者减轻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如投保人是保险公司长期从业人员,对于特定险种是了解的,就应当减轻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义务;同一保险人与同一投保人再次或多次签订同类的保险合同,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应当适当减轻③。必须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保险人不能以明确说明义务接受者的特殊性而要求免除明确说明之义务。如投保人是法官。因为从事刑事审判、行政审判的法官并不一定了解保险业务。
本案中,天安保险公司仅有投保单上由投保人亲自书写免责条款的记载和确认承诺函,还不能足以证明天安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之义务,充其量只是明确说明的初步证据。因为从这些证据上看不出明确说明的程度或效果,看不出使得投保人充分、确实地了解了免责条款的内容、含义和法律后果。
从民事证据规则来看,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与明确说明义务,其举证责任在于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至于保险人是否应当提供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或者其他证据,则可以依据具体的案情进行判断。
二、格式条款的文字语义不清或有歧义性是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前提。
合同是缔约各方当事人为自己订立的法律,自成立生效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以合同内容作为基准加以确定。当事人订立合同之际已经隐含了一个前提:当事人已经预见到了将来合同履行中的各种情况,并就此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了权利义务关系上的处理。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存在大量的歧义与空白,以致产生纷争。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语言文字本身的局限性。作为当事人表达意思的工具载体的语言文字,只是客观化的有限符号,相对于丰富的客观世界,无法精确地表示,一词多义的情况有之,使得当事人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偏差。二是当事人理性的有限性。许多情境是有限理性的当事人无法预料。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解释,只能是在处理合同纠纷过程中,对作为栽判依据的事实所作的权威性说明④。
(一)合同解释的法律规定。
合同的解释是指对合同条款及其相关资料的含义所给予的阐释和说明。之所以合同需要解释,是因为合同条款产生了歧义。合同条款的歧义性,是指当事人对合同条款含义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理解,且这些解释表面上均可以成立。
合同解释有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之分。前者是针对所有合同产生歧义时所适用的解释原则和方法;后者是针对某一类合同产生歧义时所适用的解释原则和方法。
《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该条是关于合同解释一般原则和方法的规定。根据此规定,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有文义解释、整体解释、交易习惯解释、诚实信用解释和目的解释。文义解释,是以合同条款中使用的文字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整体解释,是将争议的合同条款视为合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该合同条款与其他条款的关系、在整个合同中的位置等来解释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交易习惯解释,是按照交易习惯对合同文字或条款的含义进行解释;诚实信用解释,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探求当事人订立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充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目的解释,是按照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解释合同争议条款。目的解释是合同解释的核心原则和方法。
除此之外,《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该条就是格式条款解释的特殊原则和方法:通常理解解释(即文义解释)与不利解释。由于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的一种,《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是保险合同解释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二)一般解释原则优先于特殊解释原则。
依据《合同法》第41条、第125条和《保险法》第30条的规定,不利解释并非保险合同解释的唯一原则和方法,换言之,不利解释并不是保险合同第一顺位的解释原则和方法。保险合同作为民商事合同的一种,同样适用于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和方法,且一般原则和方法优先适用于不利解释的原则和方法。只有在对格式条款有两种及两种以上解释时,才采取不利解释的原则和方法。所谓不利解释原则,又称不利条款起草人解释,是指合同拟定方与相对方在对合同格式条款的理解、认识上有分歧时,应当作出对合同拟定方不利的解释。在保险合同中,对保险人的不利解释,实际上也是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有利解释。
本案中,“车斗未放下导致的车辆损失” 免责条款应当首先采取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进行解释。按照通常情况下对合同条款的字面意思理解加以解释,这是一种客观的解释方法,它接近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有在此方法无法确定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的前提下,才能采用其它的解释方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通常理解,应该是指一个普通智识之人在平常情境之下对于保险合的正常理解,绝不是指保险专业人士或者法律专家对于保险合同的理解,也不是普通人在十分特殊环境下对于保险合同的理解。由于保险合同技术性较强,精算技术往往不为人所了解,加之一些专业术语晦涩拗口,所以在合同履行中往往发生歧义。保险人不应以专业标准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能够充分理解上述术语。
依据通常理解解释(即文义解释),车斗未放下是导致车辆损失的直接原因,未放下的车斗与损坏的车辆之间应该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盈安运输公司认为,应该是在车斗没有卸货时未放下导致的车辆损失,保险公司才不予赔偿。而天安保险公司则认为,只要车斗未放下导致车辆损失的,保险公司都不赔偿,不论在不在卸货时。两者解释的意思并不一个致。依据目的解释,盈安运输公司投保时不可能排除自己自卸货车有别于其它货车的特有工作功能。若按照天安保险公司的解释意思,将投保人自卸货车作业中的自动卸货的合理风险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免除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风险,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权利,有悖于公平原则。依据《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和《保险法》第19条之规定,也是无效的。根据效力从优原则,当保险合同既可以解释为有效,也可以解释为无效之际,一般应该按照合同有效进行解释。毕竟,当事人缔结保险合同的初衷在于履行合同,使得保险合同成立、生效。
若按照通常理解解释仍然无法得出确定的理解时,才适用不利解释的原则和方法。本案中“车斗未放下导致的车辆损失” 免责条款,应该是车斗在没有卸货时未放下导致的车辆损失,天安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其实,本案事故发生的事实是该车辆自动卸货时侧翻,导致该车辆严重损坏。并非是车斗未放下导致车辆侧翻,而是车斗在自动卸货的正常工作过程中,由于货物自动卸载时不均衡导致车辆侧翻的,显然不受特别约定内容之约束。
作者简介:刘 斌(1962-),男,安徽众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铜陵学院客座教授,铜陵广播电视大学客座教授。
作者简介:谈春明(1964—),男,安徽众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注释:
①许崇苗、李利编著:《最新保险法适用与案例精解》,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②张峻岩主编:《保险法热点问题讲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③许崇苗、李利编著:《最新保险法适用与案例精解》,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④苏惠祥著:《中国当代合同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页。
参考文献:
[1]许崇苗、李利编著.最新保险法适用与案例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张峻岩主编.保险法热点问题讲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3]詹昊编著.新保险法实务热点详释与案例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4]周玉华编著.最新保险法条文释义与案例解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
7
- 上一篇:论在先企业名称权与在后注册商标专用权冲突
- 下一篇:浅析触电身亡的人身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