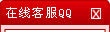以逼问报复对象住处为目的伤害他人的是手段的牵连犯
——兼谈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区别
刘 斌
内容提要: 通说认为,牵连犯属于处断的一罪,《刑法》总则没有对牵连犯规定处罚原则,除《刑法》分则特别规定外,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对牵连犯应遵循“从一重处罚”,或者“从一重从重处罚”的处罚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区分,甚至出现将犯罪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或者犯罪的结果行为与原因行为分别定罪量刑,数罪并罚的现象。当故意伤害的特定对象为多人时,易与寻衅滋事相混淆。
关键词: 牵连犯 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 区别
案情简介:
2009年4月23日凌晨2时许,王某某因琐事与张某手下的“小弟”王某在网络QQ聊天时发生争吵,王某声称要殴打王某某。王某某即电话告知曹某并请求其帮忙,曹某随即与王某相约在铜陵县景湖湾网吧见面。嗣后,曹某邀集崔某、曹某某、左某、陈某、何某、徐某等人汇合,携带砍刀、长矛、板斧等凶器。王某某、崔某先后坐车到景湖网吧探风。同时,王某邀集韦某、姚某、朱某、瞿某、张某某、戴某、赵某等人,携带砍刀、长矛、板斧等凶器,分乘三辆出租车至景湖湾网吧、县城北等地寻找曹某等人。后在景湖湾小区附近的十字路口看见坐车探风的王某某,王某等人追赶王某某至北湖新村与曹某等人发生械斗,并致朱某轻伤。张某得知朱某被曹某等人打伤后,并与参与北湖新村打架的众人商定继续打曹某等人,并电话告知曹某:“你把我底下的人干到了,既然‘游戏’开始了,那么‘游戏’就继续。”
2009年5月2日20时许,张某伙同朱某、张某某、吴某、姚某、王某、瞿某、韦某、戴某、赵某、程某等人至铜陵县五松镇北湖“梦想网吧”,见到曹某的朋友胡某等人,遂将胡某带至铜陵县亚兴焦化厂附近,逼问曹某等人的居住地,并对胡某持续殴打、侮辱、恐吓三个多小时。
2009年5月9日21时许,曹某手下的陈某、曹某某等人在铜陵市“华克山庄”KTV包厢内娱乐休闲。吴某从别人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即请示“老大”张某并得到张某同意后,邀
集张某某、朱某、姚某、王某、瞿某、韦某、戴某、赵某、程某、高某等人携带砍刀、板斧等凶器,于当晚10时40分许,分乘三辆出租车至“华克山庄”,冲进KTV包厢当场分别将陈某、曹某某砍成重伤和轻微伤。在逃离现场的途中,吴某电话向张某报告了砍人的结果。

2009年5月26日下午,韦某、王某、吴某等人得知曹某等人在铜陵县五松镇城区露面后,邀集十余人携带砍刀、长矛等凶器在五松镇城区四处寻找曹某等人未果。傍晚,吴某、张某某、朱某、王某、瞿某、戴某、赵某、程某、韦某等人被张某邀至吃饭。期间,吴某、王某将准备晚上继续搜寻报复曹某等人一事向“老大”张某请示,在得到张某的同意后,吴某、张某某、朱某、王某、瞿某、戴某、赵某、韦某、程某等人携带砍刀、长矛等凶器继续在铜陵县五松镇城区寻找曹某等人,当晚10时许在铜陵县第三中学附近发现曹某、胡某、徐某等人,并分头对其追打,致使曹某受到轻微伤害,迫使曹某跳入北湖水塘中逃生。事后,吴某将此事情向张某作了汇报。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某、韦某、赵某、程某(其他被告人已另案处理)4月23日构成聚众斗殴罪、5月2日和5月26日构成寻衅滋事罪、5月9日构成故意伤害罪。笔者认为,5月2日和5月26日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法理分析:
一、5月2日所谓的寻衅滋事是手段的牵连犯,应从一重处罚。
公诉人指控的5月2日、5月26日寻衅滋事和5月9日故意伤害,均是基于4月23日双方聚众斗殴产生的事由和恩怨。因为在这次聚众斗殴中,朱某被曹某等人打成轻伤,朱某是张某手下的人,以张某为首的一帮人要报复殴打以曹某为首的一帮人,于是在嗣后短暂的一个月内又陆续发生了5月2日、5月9日、5月26日三起伤害事件。
一般认为,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或者原因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即在犯罪行为可分为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时,如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便成立牵连犯;在犯罪行为可分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时,若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便成立牵连犯。前者如:行为人伪造了公文、证件、印章去实施诈骗,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诈骗,但其所采用的手段又触犯了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后者如:行为人窃取财物后,为了销赃而伪造公文、证件、印章。行为人的原因行为触犯了盗窃罪的罪名,而结果行为又触犯了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罪名。
本案中,在5月2日所谓的“寻衅滋事”中,受害人胡某本身就是曹某一帮的人,以张某为首的一帮人在铜陵县五松镇北湖“梦想网吧”见到胡某,遂将其带至铜陵县亚星焦化厂附近进行殴打、侮辱和恐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问曹某等人的住处,主观上是出于报复殴打曹某等人这一基本的犯罪目的,是为了追求报复殴打曹某等人这一最终的犯罪目的服务的。
牵连犯的特征是:第一、行为人实施了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两个以上的行为都各自具备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如果行为人虽然实施了两个以上的行为,但这两个行为只有一个是独立的犯罪,就不构成牵连犯。本案中,5月2日殴打、侮辱和恐吓胡某的手段行为与5月9日故意伤害曹某一帮人中的曹某某、陈某(重伤)的行为均各自具备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全部构成要件。
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出于一个基本的犯罪故意,追求一个基本的、最终的犯罪目的或原因。牵连犯所涉及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都不是行为人追求的基本的、最终的目的或原因,而是基本、最终目的或原因所派生出来的犯罪故意。本案中,殴打、侮辱和恐吓胡某的手段行为是报复殴打曹某等人这一最终的犯罪目的派生出来的。
第三、两个以上的行为必然具有牵连关系。所谓牵连关系,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数个行为之间具有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或者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依存关系。即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牵连的意思,在客观上具有通常的方法或结果关系。主观上,看行为人是否为了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或者犯罪原因而实施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也就是说,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都是在最终目的或者原因支配下实施的,才是牵连犯。客观方面,看目的行为与方法行为、或者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间有无目的与手段或者原因与结果的牵连关系。本案中,殴打、侮辱和恐吓胡某的手段行为与报复殴打曹某等人这一最终的犯罪目的是依存关系,主观上具有牵连的意思,客观上具有通常的方法。
第四、行为人的数个行为必须触犯数个不同的罪名。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数个行为触犯的是相同的罪名,即使他们之间有联系,也不能构成牵连犯。本案中,5月2日殴打、侮辱和恐吓胡某的手段行为与5月9日故意伤害曹某一帮人中的曹某某、陈某(重伤)的行为均各自触犯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
牵连犯,属于处断的一罪,《刑法》总则没有明文规定处罚原则,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对牵连犯应该“从一重处罚”或者“从一重从重处罚”,《刑法》分则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由于将陈某打成重伤,应当定故意伤害罪。
二、5月26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是故意伤害,但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根据《刑法》第293条之规定,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恣意挑衅,随意搔扰,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公共秩序,他人的人身权利、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则是本罪的选择客体。犯罪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人和物。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寻衅滋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其犯罪动机或是开心取乐,或是寻求精神刺激,或是显示威风等。
根据《刑法》第234条之规定,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和非法侵害公民身体的行为。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和身体权。犯罪的对象是专指损害特定人的身体健康。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和侵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其犯罪动机或是出于报复、妒忌,或是出于逞强霸道,或是其他纠纷引起等。
本案中,5月26日的故意伤害行为是基于4月23日双方聚众斗殴产生的事由和恩怨,是在5月9日将曹某一帮人中的曹某某、陈某打伤之后,还没有报复殴打到曹某的继续,是以张某为首的一帮人与以曹某为首的一帮人相互之间报复行为的继续(曹某、陈某、曹某某均已构成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根本不是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恣意挑衅,随意搔扰,而是事出有因,寻机报复;其犯罪动机不是为了开心取乐、寻求精神刺激,而是出于伤害他人的身体健康权和他人身体的故意,犯罪对象十分特定。特定的一帮人与另一特定的一帮人相互报复殴打,不能认为特定的对象为多人时就变成不特定的对象了。其行为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人的健康权和身体,而不是直接侵犯了公共秩序。从广义上看,很多犯罪在侵犯某一直接客体时也间接地侵犯了公共秩序。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两罪的主观动机和犯罪对象不同。前者往往是无端寻衅,打人取乐,或者显示威风等,因此侵害的对象往往是不特定的人。而后者往往是产生于一定的事由或恩怨,因此侵害的对象往往是特定的人。但两罪并无绝对界限,因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伤害后果的情况下,两罪可以转化。一般认为,因寻衅滋事致人轻伤的,仍然构成寻衅滋事罪,若致人重伤、死亡的,则应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
再从《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四种寻衅滋事行为上看,本案也不具备寻衅滋事罪的客观方面。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这里的情节恶劣的随意殴打他人,是指出于耍威风、取乐等目的,无故、无理殴打无辜者,手段残忍或多次实施这种行为。本案中,被告人王某、韦某、赵某、程某等人正是在得到张某同意之下四处寻找继续报复曹某等人,分头追打曹某等人,并非“随意”、“无故”、“无理”地殴打他人,出于耍威风、打人取乐的目的,而是事出有因,报复伤害。曹某等人也不是“无辜者”。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他人,一般是指出于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的需要,无故、无理追逐、拦截、辱骂他人,造成恶劣影响、激起民愤或发生其他严重后果。本案中的追逐、拦截也不是“无故”、“无理”,寻求精神刺激,同样是事出有因,报复伤害。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情节严重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主要是指以蛮不讲理的手段,强行索要市场、商店的商品以及他人的财物,或者随心所欲毁损、占有公私财物,数量较大或次数多,或者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使公私财物受到严重损失。本案中不具有这一行为和情节。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起哄闹事,主要是指出于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的目的,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制造事端,导致公共场所秩序受到破坏,引起群众惊慌、逃离等混乱局面。本案中也不具有这一行为和情节。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韦某、赵某、程某等人分头追打以曹某为首的胡某、徐某等一帮人,是一起事出有因、对象特定的报复故意伤害的继续,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是,由于曹某受到轻微伤害跳入北湖水塘中逃走,没有造成故意伤害罪的法定结果,因此不构成犯罪。
————————————————————
参考文献:
[1]孙国祥.刑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张明楷.刑法学(上、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赵秉志.刑法学(上、下)[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刘斌(1962-),男,安徽众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铜陵学院客座教授,铜陵广播电视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