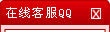小 吃 处 处
刘长峻
每年总要出差外地数次,加上探亲唔友,算是到过一些地方。因为大部分是工作旅行,数日逗留,行色匆匆,访求名胜的闲情逸致经常被不确定的行程挤压,被工作电话打断,记忆中异地的浮光掠影,很快被时间漂洗。但是尝过的外地小吃却经常在回忆里出现,特别是那些别具风味、他处所无的,每每想起,齿颊间似有余味,也许,味蕾储存的记忆更为原始和直接,所以难以删除吧。
北京吃爆肚
有亲友居京,知我所嗜,每次过访她都要带我去吃各种小吃。举凡驴打滚、艾窝窝、三不沾等等一一吃遍,一次为了让我尝尝“都一处”的烧麦,还排了半个多钟头的队。有些小吃她没有劝我尝,当然也不阻拦我,比如豆汁儿、卤煮、炒肝,可能觉她得与我们南方人口味不相宜。但在我坚持下,她带我去吃了一次爆肚。随着店中服务员一声吆喝,一盘白中略有黄褐色、切成条状的羊肚放在我的桌上,旁边一小碟香菜,一小碟芝麻酱,一碟韭菜花。羊肚蘸酱放入口中,微有脆感,却又韧劲十足,咀嚼中羊肚的肉香混合香菜的味道,弥漫口中,味道比较实在,充满咀嚼的快感,比较平民,确实不错。但一会儿快感被酸感取代——牙根清酸,咀嚼肌僵硬,嘴里就象嚼着一团麻线,太有嚼劲了。事后知道羊肚也分肚领、肚板、散丹等不同部位,脆、嫩、韧不同,初吃者可以有所选择。亲戚笑着问我怎么样,我说很好,就是分量有点多。
新疆的拉条子
在新疆出差的几个地方,街头小吃的招牌出现最多的就是拉条子、抓饭和各种名号的丸子汤。出租车师傅告诉我,拉条子是外地人的叫法,当地人就说拌面,可拌鸡肉、羊肉等,他还好心告诉我,拉条子吃完可以免费添加。坐在小吃店里,我很快就知道他的叮嘱十分多余,师傅将一整根二公分宽、一米多长的形似刀削面的面条放入翻花大滚的锅中,几分钟后迅速捞起放在中等的铝盆里,然后加上生的韭菜(紫色)和洋葱及辣油、芝麻等拌料用力搅拌、抖动,然后放在盘子里堆起一大盘。我吃的是鸡肉拌拉条子,不是新疆特产的大盘鸡,大盘鸡类似内地的辣子鸡和黄焖鸡的混合。我吃的是手撕鸡肉,大约新疆的鸡属于野生放养,味道清淡、鲜美,加上辣油的浓郁刺激,而主食拉条子劲道弹牙,拌料中的洋葱和韭菜,风味特别,滋味浓厚,让人意犹未尽,在新疆的十多天,基本当做主食,同伴要吃米饭,每天
吃宾馆40元一份的份饭,在吃过拉条子后也非常认同,天天一道吃拉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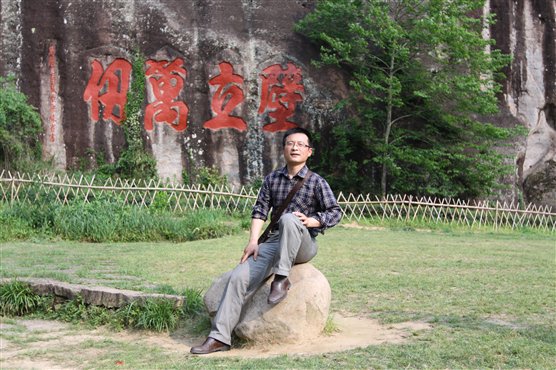
饵丝饵块
到云南最想尝尝的食物是各种菌子,可惜我去的时候是冬天,缘铿一面。在当地早餐的餐牌上饵丝饵块出现频率最高。我见猎心喜,点了腊排骨饵丝。服务员据我还有4、5米的地方一股酸辣的香味已经扑面而来,一个砂锅端上来,汤色是鲜黄色的,上面有几块腊排骨,几片翠绿的香菜叶子点缀其间,令人胃口一开。筷子在汤中一捞,类似面条的饵丝热气腾腾,入口一嚼,有点象老家的米面,但比一般的米面略窄,口感比面条黏牙,饵腊排骨咸鲜,饵丝汤辣中透酸,味浓不腻,冬日早晨喝上一碗,全身通畅,心情爽适。网上一查才知道,饵丝就是一种米粉加工的面条,类似米线但不完全一致。因麦类制作的食品古时约统称为“饼”,米类制作的为“饵”,故而得名。饵块与饵丝同源异形,是制成薄饼状的米粉,我经常在街头看到路边摊上烘烤饵块卷菜吃,摊上一般还有土豆制品,高海拔地区的土豆有红有紫,可炸可烤,口感营养都不错。多说一句,在云南汤是不放盐的,里面一般加菌干,开始很不惯,但离开云南时,我已经很喜欢喝这种略带甜味的极鲜的汤了。
个人的观感极其有限,远不足言小吃的特色。况且现在小吃也传播各地,有名的象兰州拉面、肉夹馍、鸭血粉丝汤等(南京朋友告诉我,三十年前南京没有鸭血粉丝汤)。我总以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味不同。山川风物的独特性造就了小吃的魅力,其中不但体现当地人食物创意能力,甚至还暗含了某种精神气质。日韩等国人有一个观念,所谓的“身土不二”,大意指一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其地理气候、出产的食品等也是最适宜他的。很多名人晚年最渴望的无非是家乡一碗面,每个人味觉的密码与童年、与故乡的的设定密不可分。本来想借网络上一个文艺味十足的书名给这篇小文章作标题,想想放在末尾好点。人生有味是清欢,吃货们,对不对?
——————————————————————————
*作者简介:刘长峻(1972-),男,安徽众佳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