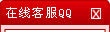如何认定保姆盗窃主人财物藏匿于屋内的犯罪形态
胡秋萍
内容题要 盗窃罪属于常见的一类犯罪,实践中,在把握其犯罪形态是既遂还是未遂上,存在着很大难度。应当结合具体个案实际状态,从受害人对财物的控制力与行为人对财物的支配力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只有同时具备受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能力与行为人完全具备了对财物的支配能力时,行为人的盗窃行为才是既遂形态,反之,则是未遂形态。
关键词 占有、控制力、支配力、盗窃既遂、盗窃未遂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8日,被告人林某通过中介公司介绍,到被害人王某家中担任全职住家保姆,负责打扫卫生和做饭。同年11月9日和10日,林某利用打扫卫生之便,先后3次从王某的梳妆台抽屉里,窃得人民币5000元、价值人民币99900元的各类首饰10件,后将现金与部分首饰藏匿于林某在一楼的保姆房间内,其余首饰则藏匿于被害人家中三楼衣帽间的隔板上。后王某发现物品被盗,怀疑是林某所为,遂向林某询问,林某拒不承认盗窃事实,后王某拨打“110”报警,警察赶到现场后,林某才交代其盗窃的全部事实,并主动交出藏于其房间内的现金5000元及首饰以及藏匿于衣帽间的首饰。
争议焦点:
一、保姆盗窃主人财物后藏于主人家衣帽间的行为属于盗窃既遂还是盗窃未遂
二、保姆盗窃主人财物后藏于保姆居住房间的行为属于盗窃既遂还是盗窃未遂
法理分析:
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可分两大类:(1)犯罪的完成形态。是指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已完全具备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在刑法上也称之为犯罪既遂。(2)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犯罪的未成形态又有多种形式: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以后,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完成犯罪的,在刑法上称之为犯罪未遂;行为人在进行犯罪预备的过程中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停止犯罪预备或者进行了犯罪预备而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着手实施犯罪的,刑法上称之为犯罪预备;行为人在犯罪预备或犯罪实行过程中或犯罪行为实行终了而结果尚未发生的过程中,出于自己的意志而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防止了结果发生的,在刑法上称之为犯罪中止。本案中所涉争议的是犯罪既遂还是犯罪未遂,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鉴于本案犯罪对象系人民币与首饰等小件物品,掩藏后不易被察觉,故当林燕取得财物并藏匿财物时,财物已失去主人的控制并置于林燕的控制之下,之后即使没有离开主人家中,也应认定为盗窃既遂。
第二种意见:藏匿位置不同直接影响盗窃的既遂与未遂。林燕的房间属于个人空间,具有独立的使用权,藏于此处的现金和首饰,已处于其实际控制之下,系盗窃既遂;而衣帽间则属于主人一家生活常用的地方,主人及其家人很容易翻到藏匿于此的物品,即林燕并未取得对此处物品的控制权,相反,主人却享有对财物的绝对控制权,故系盗窃未遂。
第三意见:主人对房屋内的所有物品均具有绝对的独立的控制权,无论是置于保姆房间内还是衣帽间,均在主人的控制范围之内,应认定为盗窃未遂。
所谓盗窃未遂,是指行为人主观上企图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客观上着手实施了盗窃行为,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盗窃未遂具有一般未遂的共性,同时在认定上又有其特殊的困难,其标准历来是中外刑法理论众说纷纭的难题。现代刑法理论中,对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主要有三种学说:(1)失控说。主张以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是否丧失对财物的占有权即控制为标准,所有人或保管人已失去控制的,则为既遂[1]。(2)控制说。认为行为人实际控制、占有了被窃物的为既遂[2]。(3)失控+控制说。认为应以被盗窃财物是否脱离所有人或保管人控制并实际置于行为人控制之下为标准,只有财物脱离所有者、保管者的控制,实际置于行为人控制之下时为既遂[3]。
笔者认为,盗窃是以特定目的为主观要件的犯罪,只有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后,使财物的所有人或者持有人失去对该项财物的控制,行为人已经支配或者处理该项财物时,就是盗窃罪既遂。刑法上的占有,不同于民法上的占有,仅指行为人对财物事实上的支配和处置,这种支配和处置具有排他性,尤其是排除了受害人对财物的事实上的占有和控制,从而使行为人取得了对财物的支配或处置。本案中,藏匿于主人家中的财物究竟被谁真正的占有,是主人具有控制力还是保姆具有支配力直接决定了盗窃行为是既遂还是未遂。只要行为人已经完全具备了支配或者处理该项财物时,就是盗窃既遂。但是,不能将“支配”简单的理解为行为人转移了财物的场所,更不能将“支配”理解为行为人藏匿了财物,而应理解为行为人事实上占有了财物,完全具备了支配或处理该项财物的能力。一般来说,只要受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行为人能够实现支配或者处理该项财物时,就应认定为行为人取得了财物。例如,雇主家的雇员将窃取的财物藏在雇主家隐蔽场所的,是否成立盗窃既遂,则看雇主会不会发现财物,看此财物是否易被发现,看雇主对财物是否还具有事实上的占有与控制力。
在认定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时,应注意的是必须根据财物的性质、形状、体积大小、受害人对财物的占有状态、行为人的窃取样态等进行判断。在本案中,保姆盗窃主人财物藏匿于房屋内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既遂,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通常认为,在特定范围场所内,物主的控制能力及于该场所内任何地方,里面的任何财物都处于其实际控制之下,物主对这些财物享有实际上的控制力,即事实上的占有。故即使保姆偷了主人早已遗忘在房屋内某个场所的物品,也是盗窃,但是之后将物品藏于房屋内某个地方,是否构成盗窃既遂,尚需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因为主人对房屋内财物在多大程度上享有事实上的控制力很难说,对于本案中这样规模比较大的房屋,主人对家中财物虽然具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和控制力,但事实上控制力所能及的范围却是有限的,如行为人若将财物藏于屋内某个秘处,主人本身就很难发现,而且行为人可以随时趁主人不备将财物带出,此时就很难讲主人对该财物享有绝对的控制力了。
据此,主人对屋内财物的合理控制范围,仍需依据社会一般观念,并结合财物的性质、形状、运送难度、社会习惯等因素综合判断。即在本案中,需借助财物的形状、性质、被藏匿位置等分析主人找到财物的难易程度,从而判断主人是否仍然享有控制力。如果财物被藏匿的极为隐蔽,或是主人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或是主人很难找到的地方,则可认为主人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综上,房屋的主人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对被他人偷窃并藏匿于屋内的财物享有控制力,需要结合案情做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笔者认为,保姆盗窃主人财物后藏于衣帽间的行为属于盗窃未遂。保姆将财物藏于衣帽间,虽然对其进行了必要的包装和掩饰,但鉴于衣帽间的用途和位置,主人是不难发现与找到被窃财物的。衣帽间是主人及其家人日常使用的场所,主人对衣帽间的所有物品均有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占有和控制力,故主人对藏匿于此处的财物并未丧失控制力。而保姆只是负责打扫卫生,除了具备可以随意进出衣帽间的便利之外,并不享有使用衣帽间的权利,其对处于衣帽间财物的控制力很有限,行为人还未有完全支配或者处理该项财物的能力。将财物藏匿于此处,并没有达到事实上的足以排除受害人占有的控制力,行为人并没有完全实现对财物的非法占有的支配能力。而保姆盗窃主人财物后藏于自己居住的房间的行为属于盗窃既遂。因为保姆房间不同于房屋中的其他地方,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主人房屋占有的控制力的一种限制。保姆房间虽然是房屋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保姆却享有同承租人一般独立的使用权与占有权。
首先,主人为了全职保姆工作方便,为其提供了住宿场所,保姆居住的房间就是受保姆实际支配和控制的,主人不会随意进出保姆房间,或是随便翻保姆的东西,因为主人知道保姆房间是供保姆睡觉休息的地方,这是保姆自己独立的空间,而主人在此阶段是无法控制的。
其次,虽然保姆的房间设在主人家里,是属于主人所有的,但保姆的单独房间只不过是相当于主人无偿租给保姆住的而已。因为同理,租赁房屋也是主人出租的,但是却是承租人实际居租和控制的,出租人在租赁期内,是失去对房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的,放在租赁房内的物品也是承租人实际占有支配的。故保姆将窃取来的财物藏匿在自己房间内,实际上已经能够对财物进行事实上的支配或处置了,即已经实际占有了财物。
最后,保姆虽然是主人雇来打扫卫生和做饭的雇工,但是其人身自由性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还是随时可以进出主人家里,当保姆窃得了主人家财物藏匿于自己房间内,之后她可以随时转移财物进行变卖或者用其他方式处理财物,因为此时,主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财物的占有与控制。
故此,保姆的房间属于个人空间,具有独立的使用权,藏于此处的现金和首饰,已处于其实际支配或处置之下,系盗窃既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一起盗窃案中,判断盗窃行为是既遂还是未遂,关键看两点:一是被害人是否已经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即是否丧失了对财物的占有,这是行为人能够实际支配或处理受害人财物的前提;二是行为人能够对财物进行事实上的支配或处理,即真正实现了对财物的占有,这是行为人取得被害人财物的必要条件。只要满足以上两点,则盗窃行为实现了既遂状态。反之,即是未遂状态。
————————————————————
注释:
[1]参见赵永林著:《我国刑法中盗窃罪的理论与实践》,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2]参见欧阳涛等著:《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0页。
[3]参见祝铭山主编:《中国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6页。
*作者简介:胡秋萍(1991-),女,毕业于铜陵学院法学院,铜陵市狮子山区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