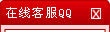缺乏意思联络不是共犯
——蔡某、严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审辩护词
刘 斌
案情简介:
公诉人安徽省微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04年2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蔡某、严某采用虚构公司、伪造证件等手段,以虚假的工程合同相引诱,骗取种某合同保证金8万元(后退还5万元);骗取宋某合同保证金15.12万元;骗取蒿某合同保证金3万元;骗取刘某合同保证金15万元;骗取随某合同保证金26.8万元;骗取陈某、马某、李某合同保证金6万元;共计73.92万元。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蔡某、严某二人无视国法,采用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安徽省微山县人民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判决被告人严某有期徒刑三年,缓期考验期五年,罚金两万元;判决被告人蔡某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五万元。
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严某亲属之委托,安徽宪达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作为本案一审被告人严某的辩护人,依法出庭为其辩护。本辩护人在两次会见被告人、认真详细地查阅案卷材料和法庭调查的基础上,提交以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采纳。
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严某构成合同诈骗罪这一定性不持异议。但是,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严某与被告人蔡某不是共同犯罪,而是各自独立的合同诈骗罪。并且,被告人严某又有诸多的从轻处罚情节。
一、蔡某、严某二人是各自独立的犯罪,而非共同犯罪。
(一)蔡某、严某二人没有实施共同的犯罪行为,不具备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
所谓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围绕着同一的特定的犯罪,互相联系、互相配合,是统一的犯罪活动的整体。不是指共同犯罪人都实施了形式上一样的行为,而是指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犯罪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一,蔡某、严某二人实施了相同的合同诈骗行为,即形式上一样的行为,但都是各
自独立的行为,并不是有机的统一的互相配合的整体。而且两人在合同诈骗的手段上有差别:蔡某是采用虚构公司、伪造证件的手段,与受害人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收取保证金;严某在2004年与受害人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收取保证金时,其所在的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南京分公司是合法存在的公司,而且严某还有公司的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任职通知书和协议书等真实的文件。只是严某所在的南京分公司因故在2005年下半年被撤销,工程也泡汤了。蔡某是以虚构主体、伪造证件的方式进行诈骗;严某是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保证金后逃匿。不仅手段不同,而且蔡某、严某二人之间也没有事先、事中、事后的合谋;不是合谋的分工合作,而是各自独立的诈骗行为。

其二,两人只是针对同一个合宁高速铁路土方工程,分别实施了形式相同的合同诈骗行为,但却是手段不同,各自独立的合同诈骗行为,绝对不是相互配合的有机的统一的共同犯罪行为。如果说两人是共同的犯罪行为,那么蔡某与严某之间签订的联营承包合同,严某收取蔡某22万元的工程保证金又作何解释呢?哪有共犯之间收取如此高额的保证金呢?蔡某当庭供述以及蔡某在侦察阶段讯问笔录中均供述:蔡某当时并不知道严某所发包的工程不存在,一年以后才发现严某所发包的工程也是假的,才知道受骗上当了。这显然充分的说明蔡某、严某二人是各自的独立犯罪行为,不是相互配合的共同犯罪行为。
其三,蔡某与严某在各自骗取受害人保证金时,两人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蔡某在骗取蒿某、刘某、随某、陈某、马某、李某、梁某、种某、宋某等人的保证金时;严某在收取种某保证金,骗取宋某保证金时;都是蔡某、严某二人各自的单独行为,事先、事中、事后,蔡某与严某都没有商量,也相互不知情、相互不在场。这一点,从各受害人的陈述,两被告人的供述上都能充分的相互印证。
其四,严某替蔡某退还受害人的保证金,是债务的转移。在受害人向蔡某要求退还保证金之后,蔡某、严某与受害人达成了由严某替蔡某退还刘某、随某、李某、梁某的保证金,是合法的债务转移行为。《合同法》第84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因为严某收取了蔡某的22万元保证金,而蔡某分别向上述受害人收取了不等的保证金。严某之所以同意替蔡某退还他们的保证金,是因为严某欠蔡某的保证金;上述受害人之所以同意严某替蔡某退还他们的保证金,是因为能够得到偿还;而不是因为蔡某、严某二人合伙诈骗了上述受害人。并且,梁某的6万元、李某的5万元,三方还履行了借条、收条的手续,严某作为新的债务人也向上述受害人即新的债权人偿还了一部分债务。既然,公诉机关认定蔡某、严某二人是共同犯罪,那么,共犯人之间有必要替对方偿还债务吗?这恰恰说明蔡某、严某二人不是共同犯罪。
(二)蔡某、严某二人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具备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
所谓共同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都知道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实施犯罪,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共同犯罪的故意,把每个共同犯罪人的个人意识和意志连接成共同的意识和意志,这是构成共同犯罪进而对共同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
其一,蔡某、严某二人签订联营承包合同时就不是共同的故意,而是各自的故意。在严某与蔡某签订联营承包合同时,严某所在的单位是合法存在的,合宁高速铁路土方工程也确有其事,严某的营业执照、授权书、任职通知和协议书等文件也是真实的;而蔡某却是虚构主体、伪造证件与严某签订合同的。并且,严某还收取了蔡某的22万元保证金。只是后来严某所在的南京分公司因故被撤销,合宁高速铁路土方工程无法进行,严某拒不返还已收取的保证金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如前文所述,蔡某在一年之后才知道严某所发包的工程也是假的,也找严某要求退还保证金。这就充分说明蔡某、严某一开始就没有合谋商量行骗,没有意思联络,是各自故意,不可能是共同故意。
其二,蔡某、严某二人各自与受害人签订合同收取保证金时,没有商量、没有相互参与,也相互不知情、相互不在场。严某与种某、宋某签订合同收取保证金,虽然是经过蔡某介绍认识的,但是,种、宋二人是以蔡某虚构公司的项目部、施工队名义签订的。签订合同收取保证金时,蔡某也不在场,完全是严某的独立行为。蔡某在2006年3月21日讯问笔录中,侦察人员问:“你和严某一起商量签订合同收取保证金的事吗?”蔡某答:“没有和他商量这些事。”同时,蔡某在骗取受害人的过程中,委任种某第七项目部施工队长、宋某第三项目部经理和陈某第二项目部经理,严某根本就不知情。上述事实,受害人的陈述、被告人的供述都能够充分印证,且蔡某在讯问笔录中和当庭供述中都说他在一年后才知道严某所发包的工程是不存在的,他找严某要保证金,严某不给,后来就找不到严某了。这能说明蔡某、严某二人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其三,蔡某将所骗取的保证金不只是交给了严某,而且还交给了其他人。蔡某在签订合同骗取保证金的过程中,他多次在讯问笔录中说到:收取的保证金,一部分交给了严某(22万元),一部分交给了戴某(7.6万元),一部分交给了黄某(13万元)等自称能够揽到合宁高速铁路土方工程中的人,作为保证金了。还有一部分自己花掉了。这说明蔡某对自称能够揽到合宁高速铁路土方工程的人都交给他们一定的保证金,对严某也不例外。这就更加说明蔡某、严某二人不是共同故意犯罪。
其四,公诉人认为蔡某拿着蔡某与严某签订的联营承包合同与受害人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骗取保证金,就认定蔡某、严某二人是共同故意犯罪,完全是主观推定。因为,本案所有的证据材料中,都没有这方面认定的证据,蔡某、严某二人均没有供述两人商量过用他们签订的联营承包合同去与别人签订合同收取保证金。合同最少是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况且蔡某、严某之间有多份联营承包合同。蔡某拿着他们之间的联营承包合同和受害人签订承包合同,无非是一种使受害人相信蔡某有此工程转包的手段,怎么能够以此为依据主观地盲目认定蔡某、严某之间就是共同故意呢?
《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然而,本案中,蔡某、严某二人的犯罪行为,只是因为同一个合宁高速铁路土方工程发包、转包的事实联系,各自实施了性质相同而手段不同的无法律上联系的独立的单独犯罪,不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因而,公诉人指控蔡某、严某二人是共同的合同诈骗罪,不能成立。
二、严某只有一起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且数额只有4万元。
(一)指控严某诈骗种某5万元保证金,不能成立。
严某于2004年9月份与种某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收取5万元保证金,虽然是经蔡某介绍相识,但如前文所述,是严某与种某的单独行为,严某与蔡某事先并没有合谋,蔡某也不在场。且种某是以蔡某所虚构公司第七项目部施工队长的名义与严某签订的。在这之前,蔡某委任种某第七项目部施工队长,给种某办理了工作证、上岗证和第七项目部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并以此已经骗取了种某诸如手续费、花销、借款3万元的钱财,如前文所述,并不是蔡某与严某的合谋,严某不知情也未参与,完全是蔡某的单独行为。
严某于2004年9月与种某签订合同收取5万元保证金时,严某所在的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南京分公司是合法存在的,合宁高速铁路土方工程也是事实。严某主观上并非出于非法占有种某钱财的目的,而是出于履行合同的诚意。即使严某主观上对南京分公司是否能够承揽到合宁高速铁路工程发生错误的认识,这恰恰说明严某当时不是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后来严某在其所在的南京分公司因故被撤销、工程因故泡汤的情况下,使严某与种某所签合同无法履行。种某向严某要求退还保证金,严某便于2004年10月份将5万元保证金退还给了种某,这就更加说明严某主观没有非法占有之目的。
虽然种某陈述是严某如不给,就到中纪委告严某,严某惧怕而退还保证金。然而,严某供述是种某说自己的儿子在西安上学需要用钱,故不再承包该工程,要求退还保证金,严某在此情况下退还了5万元保证金。而蔡某当庭供述他不知情。种某的陈述与严某之供述发生矛盾,在这两个证据不能得到合理排除的情况下,应该以“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种某的陈述不能成立。退一步说,即使种某的陈述能够成立,也不足以阻止严某不退还保证金的行为,应该说是严某主观上是愿意退还保证金的,没有非法占有之目的。
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即主观上必须具备非法占有之目的的要件,否则,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严某于2004年9月收取5万元保证金,又于10月份如数退还,时间之短,又没有足以阻止严某拒不退还的法定事由。因此,应当实事求是地认定严某主观上不具备非法占有之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严某收取蔡某22万元合同保证金,也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如前文所述,严某确实在开始时是以合法的单位、合法的身份、合法的项目(尽管严某对南京分公司能否承揽该项目发生了错误认识)与蔡某签订联营承包合同的,收取蔡某22万元保证金并不是非法占有目的的故意诈骗。相反的,蔡某一开始就是以虚构主体、伪造证件的方式诈骗严某。只是后来严某所在的南京分公司因故被撤销、工程因故泡汤之缘故没有退还蔡某之保证金。
合同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合法的公私财产所有权,而蔡某的22万元保证金是蔡某诈骗受害人的钱财,不是合法财产。而且,蔡某、严某二人之间相互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正如社会上的“黑吃黑”、“赌资”、“嫖资”一样,不受我国《刑法》之保护。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其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缺一不可,因此,“骗对骗”不可能构成犯罪。这也同时说明蔡某、严某二人之间不是共同犯罪。
(三)指控严某诈骗宋某4万元保证金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单独犯罪。
如前文所述,严某虽然是经蔡某介绍认识宋某,但是在没有与蔡某合谋、蔡某也未参与的情况下与宋某签订合同收取保证金的;宋某是以蔡某所虚构的如皋市水利安装工程公司第三项目部的名义与严某签订的。签订合同收取保证金时,严某是以合法的单位、合法的身份、合法的项目(尽管严某对南京分公司能否承揽该项目发生了错误认识)与宋某签订合同的,一开始严某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只是后来严某所在的南京分公司因故被撤销、工程因故泡汤后,严某收取宋某4万元保证金逃匿,才构成合同诈骗罪。这一事实,有宋某的陈述,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
(四)除宋某4万元保证金外,严某所欠的保证金属于民事债务。
严某收取蔡某22万元保证金,蔡某借严某1万元,实际上,严某只收取了蔡某21万元保证金。
在15.21万元债务转移中,梁某6万元债务,刘某2100元债务,随某4万元债务,严某已全部还清;李某5万元债务,严某已还6000元,尚欠李某4.4万元债务。
严某欠蔡某21万元,扣除转移债务15.21万元,严某尚欠蔡某5.79万元债务。
在15.21万元转移债务中,严某已偿还10.81万元,还欠4.4万元,加上蔡某的5.79万元,两项合计,严某共计欠10.19万元债务。
2006年11月,严某之子张某又向公安机关退还10万元。因此到目前为止,严某只欠1900元债务。
1900元民事债务与诈骗宋某4万元赃款合计,严某还欠4.19万元保证金未还。
三、严某在本案中有如下从轻处罚情节。
其一,严某是初犯,第一次触犯刑律。在此以前,严某无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与有前科或累犯的人相比,其主观恶意性较小。其二,严某认罪态度好。从被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之日起至今天的开庭审理,自始至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讲一句不实之词。不象蔡某前后供述矛盾,而且一开始有意掩盖事实真相,后又在证据面前承认犯罪事实。其三,严某表示出狱后想方设法偿还剩余的4.19万元的保证金。且绝大部分保证金已经偿还,将受害人的损失降至最低点。其四,严某年迈多病,尤其是糖尿病严某重。
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蔡某、严某二人不是共同犯罪,而是各自独立的单独犯罪,且严某主观恶意较小,人身再犯的可能性很小,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性也小。故此,请求法院对严某给予从轻处罚,建议对其适用缓刑。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采纳。
此致
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斌
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