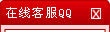浅论马尧海聚众淫乱的行为性质
余永阳
内容提要 2010年4月,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审理了马尧海等22人聚众淫乱一案,最终法院以马尧海组织和多次参与聚众淫乱而被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这是我国《刑法》自1997年修订以来第一例因聚众淫乱获刑的案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聚众淫乱罪这个在刑法中一向“沉默”的罪名,却因为“马尧海聚众淫乱案”变得沸沸扬扬,而聚众淫乱是罪与非罪的争论则成为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 聚众淫乱 换妻 废除 道德与法律
一、由马尧海聚众淫乱案引发的争议
2009年8月17日,秦淮区公安分局在一家连锁酒店的房间里将5名参与“换妻”的网民抓获,随后又牵出 17 人。这些人中,年龄最小者为1983年出生,年龄最大的则是53岁的马尧海,顶着“大学教授”的头衔,又是“换妻”游戏中的组织者,他被列为22名被告人之首。2010年4月7日至8日,南京市秦淮区法院对马尧海等人“聚众淫乱”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2010 年 5 月 20 日上午,在南京秦淮区法院进行了公开宣判;马尧海等 22 人以聚众淫乱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马尧海由于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因此被从重处罚,获刑3年6个月。其它人由于认罪态度较好,被判缓刑3年到6 个月不等的刑罚。
对于此案件的出现,引发了学术界乃至社会普遍的关注、思考和争议。以下是笔者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予以列举:
(1)著名的性问题学家李银河教授认为,“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聚众淫乱的参与者也全都是自愿参与的,因此法律不应当认定为有罪”。[1]
(2)刑法学家贾宇则认为,“是否废除聚众淫乱罪还要看民意,人们对法律的评价方式会因为对行为评价方式的转变而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这种罪名很可能会被取消”。[2]
(3)史学家葛剑雄认为,“虽然唐、明、清律都有明文规定,对公开的淫乱活动要治罪,但官府对于民间的淫乱基本是民不举官不究的,因此对于聚众淫乱,政府也不应当主动追
究”。[3]
(4)代表普通百姓的农民工歌手李路正认为,“若取消聚众淫乱罪会教坏年轻人,法律不仅不应当废止对聚众淫乱罪的规定,还应当予以加强,我们是有着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应该让青年人继承优秀文化传统”。[4]
(5)上海东方早报的记者简光洲认为,“聚众淫乱罪是在特定年代制定的一项罪名,与不少的法律法规一样,它反映了公权力对私权的过度干预,因此聚众淫乱罪应该被修改或删除,如同当年的投机倒把罪如今也被删除一样”。[5]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是不无道理的,这不仅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民意的反应,也是当今人们的性道德观念的体现。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马尧海案所引发的社会争议中,我们必须分清两个不同层次的争议,一是立法上的争议,即刑法将聚众淫乱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否合理、是否正当,或者说对刑法中既有的聚众淫乱罪是否应当予以修改或废除的争论。二是司法上的争议,概括地说,就是争论法院依据刑法关于聚众淫乱的既有规定,判决马尧海等人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以及量刑是否适当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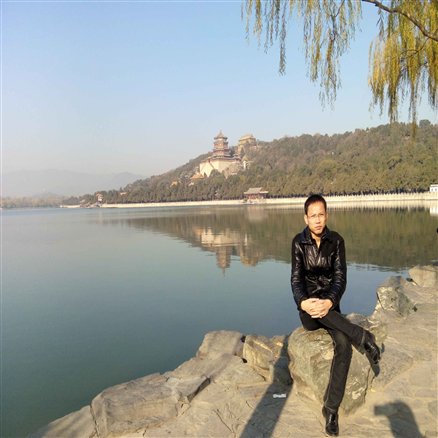
二、聚众淫乱罪在立法上是否应当予以废除
对于社会危害性是否应当被废除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刑法调整范围或适用范围的问题。对此,首先我们需要予以明确的是,由马尧海案件所引发的公众对于聚众淫乱罪是否应当废除的问题是关于立法的问题,而并不是司法的问题。我们不能将立法上的不合理而作为司法上的不合法。在笔者看来,马尧海案件引发争议、备受关注的原因不是司法上的问题,而是立法上的问题。并且,人们对于聚众淫乱罪是否应当予以修改所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围绕以下两点展开的。
(一)聚众淫乱的社会危害性。
有观点认为,聚众淫乱行为是没有受害人的行为,行为人都是自愿参与的。公民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当然也包括性器官的所有权,从而每个公民都有性的权利,性的权利作为公民个人的私权利,包括公民性自由的权利。那么,聚众淫乱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呢?根据孙国祥教授的观点“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实际造成的损害或可能造成的损害。”[6]也就是说,社会危害性必须满足“行为性” “社会性” “合法性” “危害性”这四个要素。
针对这四个要素,首先,对于马尧海案件中聚众淫乱行为的“行为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虽然有很多人认为性行为属于个人的私事,不应该由国家来加以管理监督。但是在笔者看来,任何个人的关系都会涉及到社会的关系,所以对上述观点的反驳者总会将该行为所涉及的关系纳入社会公共领域。正如有的批判家所批判的“‘没有人会是一座孤岛’,而在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不可能判识出这样的行为类别,这些行为是那些对别人不构成伤害的行为、或者那些仅仅对行为者本身构成伤害的行为。”[7]更何况,本案中的聚众淫乱行为本身就涉及社会公共领域至少是对社会公共道德的侵害。再次,“合法性”,聚众淫乱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1条第1款有着明确的规定,所以该行为也具有社会危害性所要求具备的合法性。最后,虽然该聚众淫乱的行为没有对实体的个人造成损害,但是它的确在精神上侵害了社会上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对性有着纯洁信仰的人的情感理念。在刑法中,我们一般将聚众淫乱罪归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扰乱公共秩序罪之中。这样的归类往往是以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作出的,对于聚众淫乱罪所侵害的客体,孙国祥教授认为,“本罪侵害的客体是社会风尚。”[8]对此,也有观点认为,“刑法规定本罪并不只是因为该行为违反了伦理秩序,而是因为这种行为侵害了公众对性的情感”。[9]
总之,笔者认为,虽然聚众淫乱行为并没有对他人造成实际损害,更准确的说是实际物质损害,但是其已经侵害了社会公众道德,乃至社会公共秩序,所以聚众淫乱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二)聚众淫乱的领域归属。
聚众淫乱行为的领域归属是另一个为社会公众所争议的话题。在这里笔者将这种聚众淫乱行为所涉及的领域也就是其所涉及的行为性质予以区分,主要从法律外的归属与法律内的归属这两个层面予以讨论。
1.法律外的归属。
所谓法律外的聚众淫乱的归属主要是指聚众淫乱行为是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题。道德与法律是有着明确的区分的,同时二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界问题上,二者的关系是十分模糊和暧昧的。针对这个特定案件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法律与道德适用范围上的区分,“道德领域的问题一旦进入了法律领域,就不再单纯是道德问题了,把道德问题法律化需要严格的审视,包括是否具各维护最低限度的道德需要,是否侵害了刑法上的法益,是否有惩罚的必要性等条件。法律的适用范围过广伸的手太长既不符合法治精神,更不符合公民根本利益保护。”[10]并且,在道德的适用范围的探讨上,哈特主张要区分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认为只有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才可以入法。细言之,就是我们一方面要最大程度上地保障公民的自主和自由,防止公权力过度干预公民私权利;另一方面,要维护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公共秩序。就马尧海案件来说,我们也需要对聚众淫乱的行为是属于道德领域(包括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还是属于法律领域(包括公法还是私法)进行反思,至少“马尧海顶着‘大学教授’的头衔”,这样类似的评价应该是隶属于道德领域的,而不应当作为定罪量刑予以考量的因素之一。
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德夫林勋爵在1959年与英国科学院所作的以“道德规范的强制执行”为题的演讲中指出,“正如一个被公众所认可的政府一样,一个社会所共享的道德规范对于该社会的存在而言是必要的;而用法律来强制推行这些道德规范的正当理由也非常简单,那就是法律应该被用于维护任何对社会的存在而言非常重要的东西。”依据他的观点,那么聚众淫乱行为为法律进行强制性调整是“法律职责之所在”。[11]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性观念逐渐开放,所以即使先前聚众淫乱行为属于十分明确的公共领域的道德问题也开始趋向私人化,先不讨论该道德问题是否已经完全被私人化,在笔者看来,聚众淫乱行为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其所侵害的社会公共道德的严重性变轻了,其实这并不是由聚众淫乱行为所决定的,而是在性的领域,人们对性道德的遵守要求变低了,人们更加倾向于对性不道德的容忍。其实,对于性的不道德的容忍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古代,“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内室秽乱,‘上自王家,下及士大夫家,内室秽乱,毫不为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无怪民人之淫乱也’”[12]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在笔者看来,聚众淫乱行为并不仅仅是一个私人领域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公共道德领域。那么在承认聚众淫乱行为扰乱了社会公共道德的前提下,我们就必须明确公共道德与法律的界限问题,因为违反了道德不一定违反了法律,但是触犯了法律那么行为人就一定违背了某特定领域包括公共领域的道德。也就是说,即使是某一违反社会公共道德的行为,也不一定就必须由法律来加以强制执行,而这主要取决于其侵害公共道德的严重程度以及社会公共对该行为的容忍程度。
2.法律内的归属。
与法律外的归属相对应,法律内的归属却往往为公正视野所忽视。所谓法律内的归属是指某一行为虽然属于法律的调整范围,但是其究竟是由刑法调整,还是由民法、行政法及其他部门法予以调整,这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般我们认为,几个主要部门法之间是有纵向的适用层次上的差异,这里主要是指刑法是其他一般部门法律规范的后盾之法,只要在其他法律部门没有能力予以调整的情形下,才由刑法出面干涉,毕竟刑法是惩罚最为严厉的部门法。正如前文所探讨的,聚众淫乱行为虽然没有“被害人”,但是它确实侵害了社会公共道德以及社会公共秩序,所以聚众淫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刑法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必须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刑法但书所规定的“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刑法只调整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聚众淫乱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性,这是值得商榷的,这不仅是因为聚众淫乱的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因为其是行为人行使自己性自由权利的体现,并且随着人们性观念的开放,对性道德标准的降低,使得这种严重性受到根本性的质疑。此外,聚众淫乱性为确实没有实实在在的受害人,相反,参与聚众淫乱的人往往品格高尚(除性道德以外)、生活美满,并且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高压的社会环境下找到身体乃至心灵的慰藉,以至于他们可以更好地走上工作岗位,投身于现代社会。所以,如果只是由于聚众淫乱侵犯了公共道德与公共秩序就加以刑法的制裁是值得质疑的,因为该聚众淫乱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可以通过行政法或者婚姻家庭法等其他前在的法律来予以调整,而不是一概由后遁法予以严厉制裁。
三、司法审判过程中的聚众淫乱罪
与讨论聚众淫乱罪是否应当予以修改的立法层面的讨论不同,司法审判过程中所讨论的聚众淫乱罪的讨论所关注的是法律适用的问题。因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法官应当依据刑法的既有规定对符合刑法规定的各个具体罪名予以定罪量刑。具体的来说,按照我国97年《刑法》(现行刑法)分则第301条第1款规定:“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所以只要是符合该法条所规定的聚众淫乱的犯罪构成要件即构成聚众淫乱罪。即使该聚众淫乱罪这个大前提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公正以及是否应当被废除修改,这并不是法律适用的问题,而是立法者所应该关心的问题。
对于何为聚众淫乱罪,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认为的:“聚众淫乱罪,是指聚集众人进行集体淫乱活动的行为。聚众淫乱,是指纠集三人以上群奸群宿(聚众奸宿)或进行其他淫乱活动”。[13]
笔者认为,聚众淫乱罪的定罪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特征:
(1)主体的聚众性。也就是说,该行为的主体至少是三人以上,如果只是两个人或一个人的性行为,则不可称之为“众”,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不要求有男有女,三男以上、三女以上也构成“众”。(2)行为的淫乱性。淫乱包括“淫” 跟“乱”两个词,淫不仅包括自然的性行为还包括其他刺激、兴奋、满足性欲望的行为。乱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伦理上的乱,例如男男之间的性行为,有亲属关系两个人之间的性行为等;二是时空上的乱,即多数主体(三人以上)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相互或者共同发生性关系。(3)行为的同时性。这里的同时性包括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相互或者共同发生性行为,行为的同时性是与行为主体的聚众性相一致的。(4)主观的故意性。即聚众淫乱的主体主观上是出于故意的、自愿的,而非强迫的、诱骗、暴力相威胁的。尤其要注意的是,如果勾引、诱惑、强迫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的,同时触犯了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5)条件的限制性。根据刑法规定,只对聚众淫乱的首要分子或者多次(一般理解为三次以上)参加的行为人才予以定罪量刑,而不满足该条件的仍然不能构成此罪。综上,聚众淫乱的概念界定为:“聚众淫乱,是指组织、策划、指挥三人以上共同进行淫乱活动行为或者多次参加三人以上共同淫乱活动的行为”[14]是比较合适的。
此外,有学者指出,聚众淫乱罪还必须满足侵害对象的公共性。即“只有当三人以上以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可能认识到的方式实施淫乱行为时,才宜以本罪论处。”[15]换句话说,如果该行为只是在秘密的空间而不为其他人或很难为他人所知晓的情形下是不构成犯罪的。对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公共道德的侵犯以及公共秩序的违反并不是以场所的公共性为依据。换句话说,这种聚众淫乱的行为如果只有在公共场合进行,实际上等于将该罪名变成一纸空文,因为聚众淫乱的行为一般都是秘密进行,没有人会公开聚众淫乱而等着法院的审判。当然,这种公共性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会构成犯罪,而卖淫行为本身比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要严重的多却并不构成犯罪,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公开性即对社会公共所造成的妨害。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卖淫这个行为没有公开性,只是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的广泛性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刑法对传播淫秽物品罪的制裁目的不是在于淫秽物品而是在于禁止这种传播行为。同理,聚众淫乱行为即使是在秘密场所,其仍然构成对公共秩序的妨害,只是这种对公共秩序的妨害被削弱了,更多的是间接意义上妨害,然而即使只是间接意义上的,就国家管理以及社会整体风俗道德而言,仍是不应予以忽视的。
四、再析马尧海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1979年我国《刑法》第160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1997年《刑法》分则第301条第1款规定:“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至今该法条未被废止,所以应仍然加以运用。所以依据现行刑法之规定,马尧海构成聚众淫乱罪是毫无争议可言的。他们的行为满足了聚众淫乱行为所必须的:主体的聚众性;行为的淫乱性;行为的同时性;主观的故意性以及条件的限制性。2009年8月17日,秦淮区公安分局在一家连锁酒店的房间里将 5名参与“换妻”的网民抓获,随后又牵出 17人。2010年5月20日上午,在南京秦淮区法院进行了公开宣判。马尧海等 22人以聚众淫乱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最终,马尧海获刑3年6个月,其它人被判缓刑3年到6个月不等的刑罚。
我们先不论该判决的量刑是否合理,单就马尧海等人的行为来说,无论他们从事的是换妻行为还是其他性行为的集聚(有的是单身而并没有换妻行为),只要他们满足聚众淫乱罪的构成所要满足的条件或者说要素,即行为人是聚众淫乱的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与聚众淫乱的,那么他们的行为就足以构成聚众淫乱罪,从而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当然,对于聚众淫乱行为本身构成犯罪的立法规定是否予以加以修改,笔者也更倾向于支持的态度,毕竟聚众淫乱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极其有限的,它往往以在秘密场所进行,不仅很大程度上隔绝了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直接妨害,而且它的秘密性也很难为公安司法机关所发掘。该行为虽然是对性自由权利的一种滥用,但是其本身仍是一种人本身的基本需求和基本人权。更何况,对该行为的管理、禁止完全可以通过民法以及行政法等其他前卫的部门法加以规定,而不一定只要造成公共道德的一定程度的妨害就加以刑法的制裁,这难免有公权力过度干预私权利之嫌。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公民对身体拥有所有权 [OL].http://news.sohu.com/20100407/n271356992.shtml.
[2] 贾宇.废除聚众淫乱需要社会进一步开放[OL]. http://news.sohu.com/20100407/n271356147.shtml.
[3]中国秦汉史专家.古代对淫乱是民不举官不究[OL]. http://news.sohu.com/20100407/n271356965.shtml.
[4]李路正.取消聚众淫乱会教坏年轻人[OL]. http://news.sohu.com/20100407/n271356214.shtml.
[5]简光洲.请公权力稍安勿躁[OL]. http://news.sohu.com/20100407/n271357326.shtml.
[6]孙国祥.刑法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8.
[7][英]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M]. 支振锋.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
[8]孙国祥.刑法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570.
[9][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268.
[10]梁茵.论聚众淫乱罪[D].暨南大学.2011,7.
[11][英]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M]. 支振锋.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
[12]梁茵.论聚众淫乱罪[D].暨南大学.2011,2.
[13]张明楷.刑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76.
[14]陈猛.论聚众淫乱罪[D].西南政法大学.2011,3.
[15]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76.
*作者简介:余永阳(1988-),男,安徽众佳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 上一篇:论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制度
- 下一篇: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