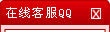四十八小时与三个例外
刘 斌
业内人士都知道“会见难”是律师执业过程中的老大难之一。在2012年刑诉法颁布之前,可以说所有的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都会遇到办案机关各种各样的刁难和阻碍。
记得有一次与陶然亭律师去周边某市看守所会见一个涉嫌盗窃罪的犯罪嫌疑人。因为不远,早上开车去,上午会见,中午前就能赶回。没有想到的是到了看守所,当我们将律师事务所会见函、律师执业证与委托书递交给看守所值班的警察时,这位上了年纪的老警察说,你们必须到我们当地的司法局盖章证明你们的律师身份后才能安排会见。很是无奈,我们只得开车前往当地司法局开“证明”,在得到当地司法局的“律师身份证明”以后再开车来到看守所会见。
无独有偶,还有一次与吴福明律师一道开车前往某县看守所会见一个涉嫌故意伤害罪的犯罪嫌疑人,这位看守所的警察更有新招,说我们是外地来的律师,必须出示个人身份证才能安排会见。这简直就是对律师的歧视与侮辱。
2012年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确立了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障碍会见权”,即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安排,这属于看守所的法定义务。其重要变化是,辩护律师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或者看守所的审批就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1979年刑诉法的两次审批撤销了。2012年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的确立,从立法上将2007年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律师会见权进行了必要的衔接,解决了1979年刑诉法与律师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与此同时,2012年刑诉法第三十七条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立了一些程序保障。首先,律师会见时有权向当事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1979年刑诉法没有这个规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律师会见时不能与当事人讨论案情。如果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向其了解、讨论案情,律师又何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律师又何以行使辩护权?律师又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行使辩护权,不仅仅是单方面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还要向当事人了解案件情况。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综合了解案情,也才能依法向办案机关提出中肯的法律意见。其次,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这意味着律师至少
可以将案件中的有关证据向当事人出示。律师也只有向当事人出示证据,才有可能核实证据。再次,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就意味着律师会见当事人是私密性的。
2012年刑诉法第三十七条对律师会见权的确立与保障,其美中不足的是四十八小时的安排会见与三类案件会见的例外批准。2012年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与第三款的规定,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会利用法律表述的漏洞来限制律师的辩护权利。

“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立法的本意应该说是积极的,是催促看守所尽快安排律师会见,律师最迟在四十八小时内能够会见到当事人。因为1979年刑诉法没有限制,看守所可以有意无意地拖延律师很长时间才安排律师会见当事人,不利于律师行使辩护权,削弱了当事人的辩护权。
2012年刑诉法作了一个最低的限制,最多不能超过四十八小时。1998年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但是实践中,有的办案机关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了安排,但往往安排的是律师在一、两个月之后会见。2012年刑诉法的“至迟四十八小时”,也可能变成所有的律师会见都拖到四十八小时以后的常态做法。这种立法表述,完全可以演化成看守所在四十八小时安排律师会见都属于合法的行为,这很明显是对律师法中对律师会见权保障的限制。
这种立法表述还存在一个问题,“至迟四十八小时”会见没有区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处的诉讼阶段。以前发生的阻挠律师会见、延迟律师会见的时间,大都发生在侦查阶段。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尤其是审判阶段,很少出现律师会见受阻的情形。由于2012年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法律表述未作阶段区分,就有可能出现三个阶段都让律师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这反而倒退了。不要小看了这四十八小时,对于有些案件的当事人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往往能改变一个当事人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2012年六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根据2012年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分别这应的是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种律师会见许可制度的设计,存在着很多缺陷。
“特别重大”的界定不明确。何为“特别重大”?尤其是贪污贿赂案件,在办案过程中,涉嫌贪污贿赂的数额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办案机关完全可以先说涉嫌几百万元,甚至更多,定性当然是“特别重大”,等查完后可能只有几十万元,甚至更少。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办案机关手里,没有一个可以把握的尺度。这就意味着,几乎所有涉案数额大一点的贪污贿赂案件,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可能。
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法律理念问题,就是如何定位和对待律师行业?之所以如此立法,其原委在于防范律师泄密,妨碍了办案机关对案件的进一步侦破。虽然从侦查的角度可以理解,但是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角度来讲,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辩护权,缺乏公正性。防范泄露案情,不仅仅是律师,所有包括办案人员在内的任何知情人都有这种条件和可能性,而实践中发生律师泄密的却极少,应该从其他制度设计上一视同仁的杜绝办案人员与律师泄密情况的发生,以保障案件侦查的顺利进行。以这种剥夺律师会见权、辩护权为代价换取律师可能泄密的情况,不仅有失公平,而且也是对律师行业的歧视。在一个共同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岂能厚此薄彼?
这三类案件会见的例外批准,没有规定哪些情形不许可会见?不许可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应当许可而不许可时如何救济?因此,应该通过立法程序加以修改,或者通过司法解释,明文规定不许可的事由、不许可的时间限制以及应当许可而不许可时的救济途径。否则,必然出现办案机关任意不许可的戾气之风。
会见权不只是律师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权利应该对等,尤其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更要有保障私权利的制度救济途径,国家公权力的法益保护功能与个人的自由保障功能必须达到相对的平衡状态。
*作者简介:刘 斌(1962-),男,安徽众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铜陵学院客座教授,铜陵广播电视大学客座教授。
- 上一篇:假如被告人真的有罪
- 下一篇:透过现象看本质——谈《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