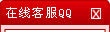假如被告人真的有罪
刘 斌
量刑程序改革兴起之前,我国的法庭审判中,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是合二为一的,法院在一个完整的审判程序中,既要解决被告人有罪无罪的问题,又要解决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其直接后果就是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无法相互独立进行,一旦选择进行无罪辩护,往往只能放弃量刑辩护,以免相互抵消、相互矛盾;而一旦选择量刑辩护,同样无法再作无罪辩护。所以,一个案件在开庭之前,辩护律师往往在“二难”的辩护思路上进行艰难而无奈的抉择。
然而,在我国司法实务中,法院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而不会轻易宣告被告人无罪,我国法院的无罪判决率处于极低的状态。因此,当被告人不认罪时,辩护律师在无罪辩护之后也会附带提出量刑辩护意见:“退一步讲,假如被告人真的有罪,请法庭注意以下量刑情节……”或曰“如果法庭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那么请法庭注意以下量刑情节……”。律师界普遍采取“如果(假如)有罪”的辩护逻辑,试图达到“两者兼顾”的最优辩护效果。但是,经常遭遇法官诘问:“辩护人,你到底认为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或曰:“请辩护人注意,你是作无罪辩护还是有罪辩护?”。这就使得辩护律师就量刑部分提出的辩护意见成为了无罪辩护的雷区,经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同时,“如果(假如)有罪”的辩护逻辑,有时候被告人的家属同样提出质疑,埋怨辩护律师,得不到被告人家属的理解。
2010年10月,随着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颁布施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我国正式确立并推广开来。根据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法庭调查开始分为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两个阶段,实现了证据调查的相对分离。前半部分调查无罪证据,后半部分调查量刑证据;法庭辩论也分为两个阶段,即定罪问题的辩论和量刑问题的辩论。前半部分由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展开辩论;后半部分则围绕量刑幅度和种类展开辩论。这标志着量刑辩护的理念和实务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般来说,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辩护方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典型的无罪辩护由于被告人自愿认罪而丧失了存在的空间,辩护律师的主要职责即在于量刑辩护。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量刑程序改革中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初露端倪,即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使得辩护律师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根据量刑程序
改革的要求,辩护律师必须在定罪问题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后,参与量刑问题的审理活动,针对控诉方的量刑建议发表量刑辩护意见,但后者都不可避免地冲击着先前无罪辩护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辩护律师仅选择无罪辩护而放弃量刑辩护,则会在被告人被宣告有罪之后丧失提交量刑证据的机会,最终无法促使法院作出轻缓的刑罚。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二款“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的规定,对量刑程序改革略有涉及,但是,坦诚而言,这并未触及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存在的矛盾。
从理论上说,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一方面,量刑辩护是以有罪裁决为前提的,纯粹的无罪辩护排斥任何形式的量刑辩护。无罪辩护意味着辩护方对控诉方指控的事实或罪名存在异议,只有当法庭裁决被告人有罪之后,辩护律师才需要对量刑发表辩护意见。辩护人如果在请求法庭认定被告人无罪时就要求从轻量刑,则无疑削弱了辩护律师对被告人所作的无罪辩护的可信度。另一方面,辩护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应当尽忠于当事人利益,既然被告人在与辩护律师协商之后仍然不认罪,则辩护律师自当着眼于无罪辩护。如果被告人不认罪而辩护律师却进行量刑辩护,则表明其默认了被告人有罪的事实,不仅无法有效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第二公诉人”的角色,与辩护制度之内涵北辕适楚。
英美法系国家,量刑辩论是在定罪以后独立进行的一个独立程序。如果法庭认定被告人无罪,就不需要再进行量刑辩护了;如果法庭认定被告人有罪,就启动量刑辩护程序。两次开庭,两个独立的审判程序。换而言之,陪审团或法官先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在有罪裁决作出之后,法官才会根据各方提交的量刑信息和量刑证据宣告被告人的最终刑罚。这与我国确立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不同,法庭是在定罪辩护程序尚未宣判之前,再进行一个量刑辩护,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种情况下,量刑辩护只能建立在假定有罪的基础之上。同一个法庭审理,辩护律师先作无罪辩护,之后在假定有罪的基础上再进行量刑辩护。换而言之,法官需要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分别交叉审理定罪和量刑问题,且不会就定罪问题首先作出专门的裁决,辩护律师进行量刑辩护也就无法完全不脱离无罪辩护。故而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并没有完全解决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如果(假如)有罪”的辩护逻辑,对量刑辩护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庭前准备活动看,辩护律师重视无罪辩护而忽略量刑辩护。在两种辩护形态存在优先次序的观念下,由于被告人不认罪故而辩护律师着力酝酿无罪辩护的思路,处于次级地位的量刑辩护或多或少地遭遇寒流。被告人由于激情亢奋而无法悉数告知本案可能具有的全部量刑情节,辩护律师也不会积极引导被告人充分做好次级地位的防御准备,量刑辩护思路即是头绪万千也只化作辩护词中的寥寥数语,在无罪辩护词的慷慨激昂下悉数相形见绌。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中也就主要收集定罪证据和涉及法定量刑情节的证据,忽视了众多事关刑罚裁量的酌定量刑情节及相关证据。
第二,从庭审过程来看,量刑辩护得不到充分展开的空间。根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要求,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定罪、量刑问题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先后进行,并无主次之分。但实践中,定罪事实的审理占据了庭审的大部分时间,而审理量刑问题时法庭因时间、精力等原因就略显仓促,辩护律师无法就本案的各项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进行充分论证,量刑辩护的空间因定罪审查活动的优先性而受到压缩。
不仅如此,辩护律师同时进行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也略显左支右绌,无法在审理量刑问题之前申请休庭,就接下来的量刑审理活动再次进行防御准备,会因精力、时间所限而处于被动应付的境地。特别是在定罪审理中出现新证据、新情节的案件中,控诉方可能提交一份辩护律师事先未获知的关键量刑证据,或者被告人当庭表达了退赃、与被害人和解的意愿,等等,此时辩护律师尤其需要申请休庭来调查核实新证据或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但现行法律却并未就此作出规定。
“如果(假如)有罪”的辩护逻辑,在我国现行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下,确实能提请法庭关注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但却不足以根本落实无罪推定原则在定罪环节对被告人的保护。在英美法系典型的定罪量刑分离的审判之中,各种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在定罪裁决作出之前是不得进入陪审团或法官视野的,其目的就在于贯彻无罪推定的理念,通过公证审判来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尤其是那些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譬如被告人的一贯表现、是否有犯罪前科等等,如果在定罪程序中就在法庭出示,则必然对陪审员和法官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产生影响。所以,实务操作中尽管辩护律师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可以提交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但同时也必须就控诉方提交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各种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这些信息则不可避免地给法官心证造成污染。
特别是在庭审中辩论的环节,如果辩护律师想要主张被告人无罪,他就必须申请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并当庭释放。由于辩护律师并不能确定法庭最终会作出什么样的裁决,所以他必须针对控诉方的量刑建议发表量刑意见,向法庭表明被告人如果被判处有罪应当适用刑罚的种类和幅度。辩护律师这一主张本质上就没有逻辑上自洽性,既然要求法院宣告无罪,又为何要就量刑的具体种类和幅度发表意见,后者意见越详细越合理反而表明无罪辩护多么苍白无力。在法院宣告被告人有罪之前,辩护律师的量刑辩护意见却已然削弱了无罪推定原则对被告人的保护,这种负面影响竟是由于辩护律师行使量刑辩护权不可避免地自我损害,“如果(假如)有罪”这一逻辑对此手足无措。
我国现行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辩护律师则必须按照法律要求同时参与定罪和量刑问题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又必然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如果辩护律师只进行无罪辩护,将会丧失提交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的机会,其结果将是在被告人被定罪之后,辩护律师不会再有专门的量刑程序来就本案存在的法定、酌定情节再次发表意见。由于辩护律师无法确定法庭是否将会作出有罪判决,导致律师一方面竭尽所能攻击控诉方的证据疑点或逻辑矛盾,但同时又不能不被动的参与量刑问题的调查和辩论。如果量刑辩护不充分,则无法反驳控诉方的量刑建议;反之,辩护律师就量刑问题的慷慨激辩都会冲击先前无罪辩护的效果,使得法官认为辩护律师已然承认被告人是有罪的。这就是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给量刑辩护造成的问题症结之所在。
量刑程序改革虽然为量刑辩护带来了前所有的契机,但是这种量刑辩护目前尚未发展成熟。虽然部分原因在于律师本身执业技能和法律素养有待提高,但是症结却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束缚了量刑辩护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它已经成为限制量刑辩护的一个美丽的法律陷阱。所以,笔者主张,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或者在被告人原本认罪而当庭却不认罪的案件中,应将定罪、量刑程序完全分离,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构建两个完全独立的审判阶段,即定罪裁判阶段和量刑听证阶段,而中间应该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提供必要的时间和便利,让控辩双方对量刑问题都可以进行充分的防御准备。因为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的完全分离是实现各自独立价值的唯一途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交叉进行的尴尬局面。
*作者简介:刘 斌(1962-),男,安徽众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铜陵学院客座教授,铜陵广播电视大学客座教授。
- 上一篇:揪心的物业费
- 下一篇:四十八小时与三个例外